目录
快速导航-

卷首语 | 生命起源:科学探索中的终极奥秘
卷首语 | 生命起源:科学探索中的终极奥秘
-

聚焦 | 蝶羽绽放
聚焦 | 蝶羽绽放
-

聚焦 | 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
聚焦 | 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
-

聚焦 | 在大洋深处探寻生命源头
聚焦 | 在大洋深处探寻生命源头
-

聚焦 | 地球何以拥有如此完美的生命
聚焦 | 地球何以拥有如此完美的生命
-

发现 | AI为搜寻外星文明拓宽视野
发现 | AI为搜寻外星文明拓宽视野
-

发现 | 奇思妙想的微波动力飞机
发现 | 奇思妙想的微波动力飞机
-

发现 | 栉水母:海洋中的“隐形”生物光使者
发现 | 栉水母:海洋中的“隐形”生物光使者
-

发现 | 小诸葛漫“话”天气之雨影效应
发现 | 小诸葛漫“话”天气之雨影效应
-

辟谣 | 辟谣
辟谣 | 辟谣
-

趣玩 | 海底火山:手动制造“岩浆喷发”
趣玩 | 海底火山:手动制造“岩浆喷发”
-

趣玩 | 多姿多彩的观赏凤梨
趣玩 | 多姿多彩的观赏凤梨
-

趣玩 | 蟾蜍观察日记:它们喜欢挠痒痒吗
趣玩 | 蟾蜍观察日记:它们喜欢挠痒痒吗
-

人文 | 结茧:桑姑盆手交相贺,绵茧无多丝茧多
人文 | 结茧:桑姑盆手交相贺,绵茧无多丝茧多
-

人文 | 古人也戴眼镜吗
人文 | 古人也戴眼镜吗
-

人文 | 未来水世界
人文 | 未来水世界
-

人文 | 最好的颜色
人文 | 最好的颜色
-

成长 | 拿什么来填补你的“空心”
成长 | 拿什么来填补你的“空心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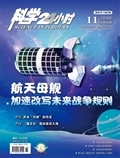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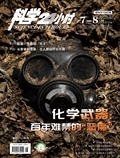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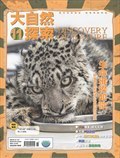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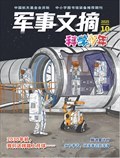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